视医学为文化,医病也医“心”
2014-09-17 文章来源:环球医学 我要说
医学是不是一种文化?文化是个大而玄的词,定义也众说纷纭,据统计不下二百种。往大了说,它囊括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,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在治疗人体伤病方面的分支——医学。不过,在实际操作中,文化远不是那样八荒六合,无所不包;医学与文化还是有很明晰的分野的——多元化的文化,一元化的医学。
不去探究这些复杂的概念,其实,医学也应该是一种文化,靠文化承传,靠文化立命。
疾病命名:尊重前人的世界文化
川崎病是在1967年时第一次被一位日本的儿童医生所发现,并以他的名字命名。阿兹海默症最早由德国精神科医师及神经病理学家爱罗斯·阿兹海默在1906年描述记录,之后并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很多综合征都是由人名命名的:美尼尔氏综合征、帕金森氏综合征、范可尼综合征、马凡综合征、特纳综合征、唐氏综合征、费尔特氏综合征……
每次在描述疾病时,我们缅怀、感激医生。诸如此类的以发现或发明者命名,已成为尊重前人的世界文化。
医学是一代代先贤聪明才智的积累,是依靠著书立说或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技艺。只有感恩先师和前辈,医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。
必要的行医仪式树立医生威信
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,每逢出诊必沐浴更衣,梳理装扮。她身上体现了医生临诊病人前的职业神圣感。
也有一些医生不注重仪式,甚至连必要的诊疗程序也视同儿戏。某患者因胸闷住某医院,三天后惶恐地打电话询问医生朋友:“明天上午就要做心导管了,怎么还没有一位医生听过我的心脏?”其实住院三天,医生为她做了一系列详细的辅助检查,并与家属沟通好要做PTCA。虽然事后证明管床医生导管技术娴熟,治疗效果也不错,但在诊疗过程中居然没用听诊器听诊心脏。且不说缺失基本医学操作的规范性和病历采集的真实性,至少让病人没有经历医生亲临床边这个不可或缺的仪式。
作为一种维系生命和灵魂的职业,除了必要的医学程序外,带有神圣感的仪式也绝不可形同虚设:查房的站姿、望诊的眼神、问诊的语气、听诊的神情、叩诊的手法、病历的格式等等。在这些仪式行使过程中,除了收集到必要的医学信息外,也展示着医生对生命的尊重和病人的关爱。仪式是安抚病人情绪的魔杖,必要的行医仪式树立的是医生的威信。
心灵向往有时可改变一些疾病的转归
偏方总是给人一种“无厘头”的感觉,但“信则灵”体现着医学关联和人文力量——心之所向,神之所往。
我们所谓经过严格训练的医生,不也是在滔滔不绝地向病人“兜售”我们笃信的科学方法吗?而其中一些科学方法后来又被循证医学或事实证明是错误的。比如,早年提出定时定量科学喂养婴儿,最后返璞归真为即时母乳喂养;更年期雌激素普遍应用、糖尿病要忌糖和甲亢要忌碘等,也都曾被医生们坚定地执行。
所谓科学合理的治疗措施,往往在那些未被说服的病人身上无法奏效。任何疗法都有1/3的心理暗示作用,心灵向往有时可以改变一些疾病的转归。长期以来,对病人心理向往的忽略和对病人社会属性的无视,自认为正统的医生并未意识到这有何不妥。
现代医学前一只脚刚踏出了半巫半医的丛林,后一只脚又陷入技术迷信的泥潭。迷信和信仰可能是不同话语体系的共同体。对于心理停留在迷信层面的病人,应当变换思维方式尊重他们,鄙视病人的无知或许是医生的无知。对于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医生,也要启蒙他们的人文修养,过度依赖技术其实就是一种迷信。
没有文化的医疗技术是生硬、冰冷和乏味的重复。视医学为文化,医病也医“心”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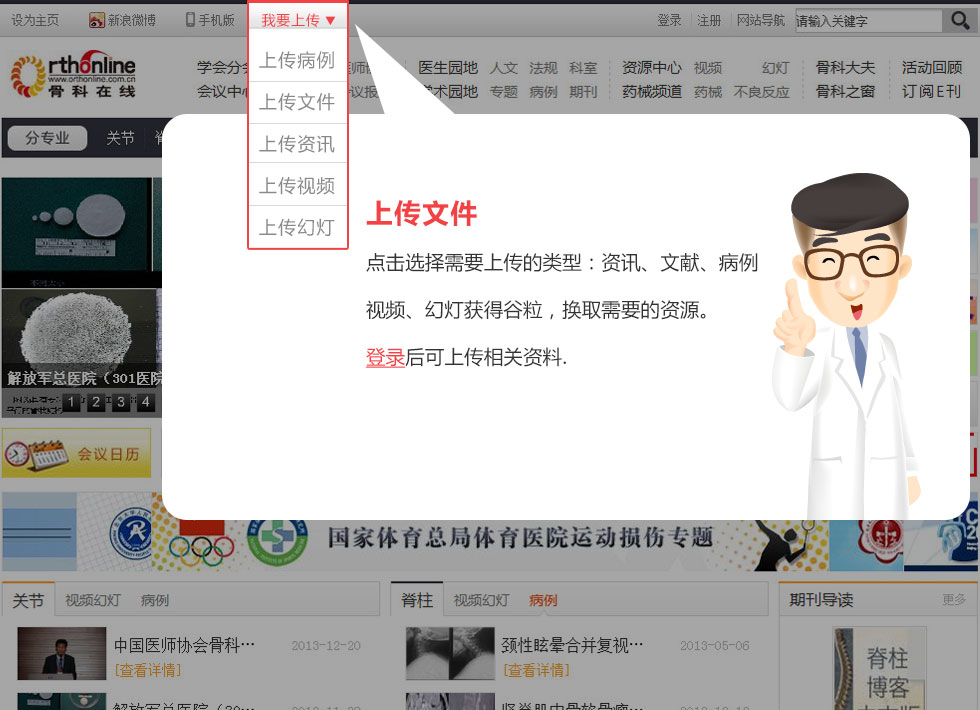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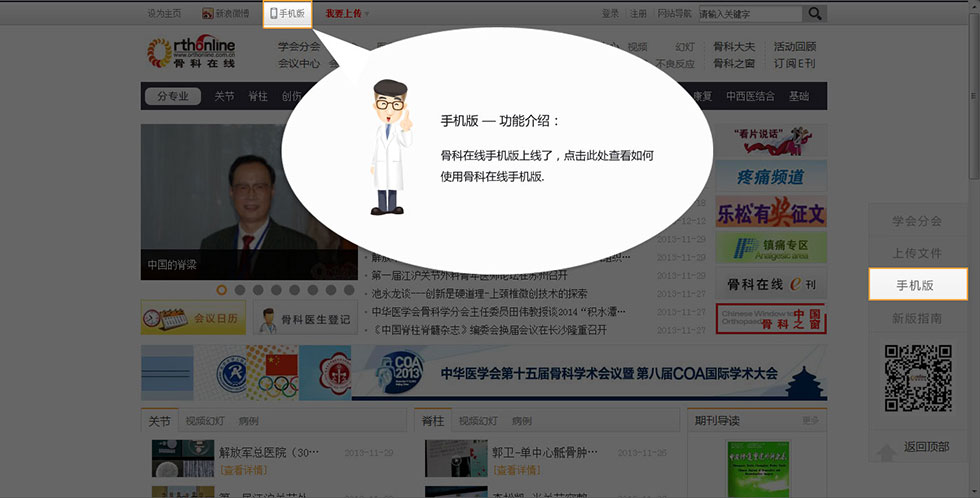

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256号
京公网安备11010502051256号